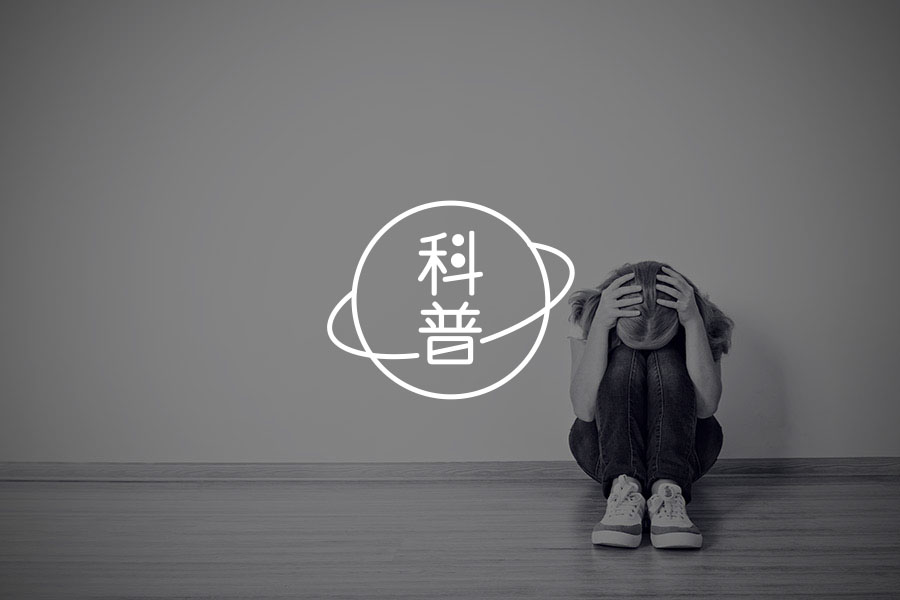
作者:陈彬华
来源公众号:彬华同学(ID:asthedusk)
特别想吐槽一下每逢社会事件、自然灾害都要前仆后继仿佛饿虎扑食的某些机构。借由这个机会,也顺便谈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培养的一个品鉴能力。
当然大家在感官上很容易分辨出,有些机构几乎纯粹是借机拓展影响力(提供的东西并没有可及性或者对应性),有些机构是希望做好事、顺便也推广一下,还有些机构几乎就是一腔热忱,加入到其它机构或是活动中去做也完全乐意。
虽然发心非常非常重要,但很多时候我们也没法臆测。不过,到底做的是什么事,那这还是完全可以看的。发心再好,好心办坏事也是种伤害。
这种“练手”风气是有历史渊源的。据古学斌老师的文章说,汶川地震的灾区心理咨询“横行”,素有“防火、防盗、防心理咨询”的说法,还有许多专家去了灾区收问卷、收集故事,挖起来大家的伤痛又得不到回应,反而伤得更深(古学斌,《灾难、名利场和自省》)。
做精神分析的朋友应该受训里边就有强调不要急,而一些做认知的朋友可能觉得是自己发挥作用的时刻。然而Bonnano指出,基于认知模型的干预方法,对经历过创伤事件并处于复原状态的人来说,实际上可能会增加她的创伤压力反应(转引自《重建应对创伤的心理弹性》)。
当然这个证据质量可能还不够高,个人的重点主要放在“复原”这个关键词上。多引用古学斌老师的一段话:
中国老百姓灾后表现出来的那股韧劲,绝不是坐在心理咨询室的专家们可以想象的。还有,支撑他们生命存活的动力到底是什么呢?什么样的支持对他们来讲才是有意义的呢?这些心理专家们未必都懂。
灾后的应激,实际是对非常规事件的正常反应。对于大多数人,在现实困难解决、人际支持恢复之后,并不会发展出创伤后应激障碍。我们要对人的韧性有更多的相信。
所以曾奇峰老师在关于“疫情中的无力感与控制”的讲座里讲到:
我们不能够预设别人在事件中一定会有很大的创伤。所以我们可以采取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被动的状态,就是等着别人来找我们。一项研究表明,美国911事件后,出现创伤的人中,被心理医生干预的人可能最后恢复的更慢一点。我们推测一下中间的原理是什么?也许是自然痊愈的力量,或者说是天道,可能比人为的干预效果更好。什么情况下才需要我们出手?就是他已经没有办法自然的康复了,这时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专业知识给他们帮一下忙。
另外,重大的丧失、反复的伤害、长时间的受困,确实有可能发展成创伤。同时,对于有基础情况的朋友,灾害也可能成为一个导火索导致症状复发或恶化。这使得灾后的干预有一定的立足点。
那么如何干预?许多人都有提出过解决方案,我来列举一些。
早期来说,重大事件压力管理(Critical Incident Stress Management, CISM)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它的核心方法是关键事件压力解说会(CISD),也就是让救援人员或者其它的协作者带着受灾者谈论自己对重大事件的感受和反应。这套方法曾被广泛运用于美国救灾、援助工作中。
CISM一度非常风靡,继而有许多的研究。既有研究发现CISM有效,也有研究发现CISM没有效果,甚至有研究发现CISM可能造成负面影响。之后就有两个质量不错的荟萃分析,前者评估了七项研究,后者分析了十一项研究。结果一个结论是没有接受CISM和接受非CISM干预的个体表现要好过接受CISM的个体,另一个结论是CISM不能减少困扰,也不能预防PSTD(转引自EMS Myth #3: Critical Incident Stress Management (CISM) is effective in managing EMS-related stress)。
后续大量的研究发现了CISM的有害性。2002年,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与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等机构、部门联合审查,决定不将CISM作为推荐的早期干预方法。
当然现在ICISF还在卖课,无国界社工上就有他们危机介入证书的课程。他们在个体部分实际删除了最开始CISM模型里边被认定在个人工作中有害的CISD技术(报告自己对关键事件的情绪和反应)。而在团体危机介入中还有保留Defusing的技术。但Defusing在团体中的作用怎样,其实也很难说,我随手搜了下13年的RCT实验,说的是做了CISD对比光做筛查,酒精滥用显著更少,而对比光做教育,生活质量更高(Group critical incident stress debriefing with emergency services personnel: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总之CISM现在应该是有所发展,但已经过了它的黄金时代。现在更为流行的是心理急救技术(Psychological First Aid)。心理急救我之前其实有介绍过,在疫情期间还有蛮多人的阅读。
其实心理急救的提出时间很早,大概在20世纪中,比CISM的20世纪末要来得早。但一直到9-11事件后才蓬勃发展起来。而它的地位也是在CISM落下神坛后上去的。
在WHO的《现场工作者心理急救指南》还给CISM再鞭了尸,提到:2009年,世界卫生组织 (WHO)精神卫生差距行动规划 (mhGAP)指南发展组评估了心理急救和心理解说的相关证据,并总结为:应该向刚刚经历创伤事件而处于极度痛苦的人们提供心理急救而非心理解说。
这里的心理解说就是以CISM为代表的方法。
有趣的是,WHO强推的心理急救,其实证据水平也不是特别好。13年在灾害健康的期刊上还有个文章在呼吁,以心理急救的“热门”程度,我们急需要它有与之相符的证据水平。因为从证据质量的角度上讲,几乎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心理急救在实现其目标上的有效性(Psychological First Aid: Rapid proliferation and the search for evidence)。
之后我又看了更大规模的荟萃分析,结论其实蛮没意思的,就是没足够证据。不过里边的讨论挺有意思,有讲到大家对循证有偏见,就算心理急救是一簇方法,我们也可以分别找各个部分的有效的基础等等(A Systematic Literature Search on Psychological First Aid: Lack of Evidence to Develop Guidelines)。
虽然没啥证据,但是大家为啥还是会推崇心理急救呢?这里面自然也和权力、话语相关,不过其中一个很积极的部分是,心理急救很多时候像一个知情与科普,让大家了解到:原来还有创伤这么一回事,原来我这么说可能不大好等等。
偏手册的那种循证研究,某种程度上和心理急救本身那种民众运动的气质会有不合的地方,但也并不是就需要去排斥。如果对于心理急救做更偏向公共卫生的研究,不知道结论是怎么样的。目前我还没有做这方面的检索。
说到这,其实对于这个部分,我讲有点偏多了。但为什么要多说呢?是因为我查资料之前我也不懂,而且我知道很多人都不懂。
CISM的认证课程出来了,可能大家奔着国际认证就上去了。我自己也有这样的倾向,但钱和时间都有限的,做一番功课是很重要的。而你要把一套东西,用到人身上,你要去推广的时候,你更要去确认:我做的东西会不会给人造成伤害?我花这么多时间、精力去做,对人有没有效果?
另外,有一些机构招募志愿者去做心理援助,或者去做线上社会工作。其中有一些伙伴可能是第一次做一线服务。研究是发现,实习治疗师和成熟治疗师的治疗成效差异并不大,但实习治疗师也是经过了至少半年一年完整训练以后在督导的支持下实践的。在一些危机情境下,没有危机相关受训的咨询师都未必胜任;加之整个支持体系和督导资源有限,这时候的服务,有时多少有些害人害己。
总而言之,作为社会心理工作者,我不那么推崇循证实践,但这绝对不是不顾证据、不讲证据。社会行动上,循证有时很难跟上行动的步调,但也不是不要看证据;而在干预层面,循证实践更是大有可为。
心理急救这个词真的蛮好的,你要是没有急救的训练,你把人晾在那里打电话给120更合适一些。你乱动人家,人家肋骨可能要被你戳进肺里了。偏方有时候也挺有用的,但是救灾就别用偏方了,把人给害死咋办?
有时候做咨询,就像是咨询师与来访一起探索、一起探险,甚至是创造彼此的一套语言、独一无二的疗法。每周进行的一些练习,一些想象和意象,还有做出的一些些调整,都像是一场实验。但在危机关头,还是别做实验了。创伤知情、赋权、多元和循证,从这些点出发,干脆一点、确定一点。大师是能玩出花来,但我们在关键时刻还是谦虚一点为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