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直以来,“神经病”这个词在骂人吵架中的情绪发泄作用要远超过它所指的实际意义。
“你是个神经病,所以我不和你一般见识。”
“你有(神经)病,所以我要离你远一点。”
仔细品味,这个词实质上也携带着鄙视和恐惧的意味。在日常用语中,它几乎就是指“有精神疾病”的人。
人们对精神病人一直抱有一种“非理性的恐惧”,也许因为精神疾病患者所表现出来的“不可控性”。
假如有人发现自己患上了“精神疾病”,自己或家属很可能会有强烈的病耻感,在思想上否认疾病的存在,甚至会采取一些行动来阻碍治疗。
一方面,仍有相当一部分人不了解心理咨询/治疗工作的存在意义,不知道这些工作具体能为人们提供什么样的帮助;
另一方面,那些已获得诊断的精神疾患人群中,有相当多的一部分“相信”自己需要终身服药,对心理咨询/治疗抱有一种非常悲观的态度或“无用”的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国内目前的精神卫生服务和保障系统发展水平的制约,有特殊的社会背景。
但真相是怎样的呢?心理咨询/治疗真的有用吗?它们对治疗精神疾病是有效的吗?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从一些不同的角度来了解这些问题的答案。
01
精神病院的故事:
被一个实习医生治好的“陈年病患”
Brett Kahr医生在他的临床案例集中,记载了他和精神分裂患者Steven Froggit(化名)一起工作的案例。
开始工作时,Brett还是一名精神科的实习医生,他准备一起开展工作的病患Steven那时40岁左右,在精神病院已生活了20多年。
Steven Froggit是精神病院的“最危险”病患,受到妄想和幻觉的影响,他曾多次妄图杀害精神科医生。他的精神分裂症呈现出紧张型和偏执型交替出现的特点。
在漫长的紧张症期间,他整天像一具“真”的尸体那样躺在床单下面,一动不动;到了同样漫长的偏执期,他展现出多种可怖的被害妄想:被火星人强奸,被士兵的刺刀刺中肛门,头脑中的思想被BBC在晚间新闻档期广播等。

除此之外,Steven认为自己是一只住在猪圈里的猪。他拒绝洗澡,个人卫生症状非常糟糕。护士们在他的对抗中感到筋疲力尽,几乎放弃了帮助他改善个人卫生状况的努力。
这就是我们的个案Steven Froggit在与Brett医生一起进行心理治疗工作之前的初始状况。而当时,在一个药理学占主导地位的机构里,从未有人尝试过为病患提供“心理治疗”。
Steven和Brett医生无疑都是幸运的。作为一个实习医生,Brett的想法和对精神分析的兴趣得到了当时的精神科医生支持,而Steven并不排斥接受这样的“私人会谈”,对于只见过几次面的实习医生Brett,Steven有一种“天然的喜欢”。他对精神科医生说:“我喜欢Brett,私人谈话会很好。”
于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们有机会一起开展工作,开始了长达3年,每周三次的高频心理治疗。
和Steven这样的病患建立工作同盟是困难的。好在,治疗的进程总体上是稳定的。
最初,Brett医生尝试尽可能多地了解清楚Steven的妄想和幻觉材料,形成一个更为连贯的画面。从细节中穿入Steven的世界,Brett越来越能够了解到他的患者一直在承受着怎样的恐惧和痛苦——那些正常人无法理解的可怕幻觉,在病患的世界里却是真实的。
Brett对Steven妄想中的细节所展现的好奇心起初遭到了他的嘲笑,但他依然坚持参加着每周三次的治疗。不知不觉中,这种支持性的心理治疗为Steven带来了变化,他不再那么语无伦次、咄咄逼人,不再用他爆炸性的妄想材料来“轰炸护士”。
与此同时,Brett医生没有停止对Steven的关注和了解。他开始查阅Steven的医疗档案,不放过任何可能帮助他理解病患的细节。他甚至在那些无人问津的更早期医疗档案中,找到了关于Steven的最早病例记录,包括一些旧信件和文件,尝试着重建Steven的生平。
Brett医生开始和Steven一起阅读这些资料,探索Steven的妄想之下隐藏着的秘密。在这个过程中,Steven终于慢慢从精神病患的“壳子”中现身出来,开始越来越多地展现出真实的自己。

Brett认为Steven对自己的妄想“症状”和早期经历之间的联系,了解得比他通常透露的要多。只是在透露更多之前,他需要测试医生的可靠性,忠诚和同情。也就是说,是治疗关系的质量决定着Steven是否愿意在探索自己的道路上更进一步。
18个月以后,Steven的行为举止已经不再那么疯狂,他越来越清醒,不再感到自己“是”个僵尸,也不再做出攻击行为。在精神科医生的允许下,他停止了药物治疗。Steven开始参加医院的园艺小组,个人卫生状况也越来越好。
治疗仍在继续,但中途Steven因为父亲的突然死亡一度退回到了“僵尸”状态。
有两三个月的时间里,Brett只是陪伴在Steven的床边坐着,他告诉床单下的“僵尸”Steven他来参加他们的治疗了。他试着做一个普通人,没有给出任何诠释,只是用自己的“存在”向Steven传递出一种极大的允许和陪伴。
七八次之后,史蒂文竟然开始从床单里往外看,有几秒中,他们的目光相遇了。
三个月后,Steven又恢复到了父亲去世之前的状态。他开始和Brett谈论他的哀伤、遗憾,在他面前哭泣。他也告诉了Brett更多自己的传记细节,比如关于母亲的部分。
Brett开始了解到,Steven的母亲会在她自己感到痛苦的时候殴打Steven,对他尖叫,并定期给他的灌肠。此外,她曾经拿着一把切肉刀追赶Steven,并大声地喊着“我要杀了他!我要杀了他! ”
随着对Steven早期生活中的创伤细节的了解,Brett越来越能够理解Steven曾经的妄想中所呈现的那些与死亡的斗争。
经过三年的工作,Steven已不再报告任何妄想,也不再有暴力行为。他获得了一份园艺助手的工作,不再需要精神药物。他花很多时间听唱片,尤其是德国军事音乐。Steven后来一直住在精神病院里,对他来说,已经没有其他的地方比那里更像家了,毕竟他已经住在了那里20多年。
在开始与Steven的工作之前,Brett曾经做过两个梦:在一个梦中,他被纳粹折磨,但活下来了;在另一个梦中,他吞下了一个剃须刀片,但是活下来了。
26年后,当他回忆和总结Steven的案例时,他意识到了自己的梦,可能是一种难以解释、无法言说的“反移情”证据——这些梦代表了他在治疗之初,可能已经感知到了Steven充满“杀婴恐惧”的内心世界,尽管那时他还不能完全理解。

Steven的案例向我们展示了支持性的、稳定的心理治疗工作对于疗愈的重要意义。Brett所给予Steven的稳定陪伴和支持,和在其中灌注的关注、尊重、同理,是让Steven恢复正常的重要因素。
也许,Steven可以代表那种通常会令人恐惧的“精神病人”。但即使是这样严重的病人,在稳定的心理治疗的帮助下,都可以达到停药、恢复正常功能的状态,我们对于心理治疗能否治愈精神疾病的质疑也许应该停下来,反思一下了。
真正促成疗愈的因素,是在关系中展现的爱——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全然关注、去“看见”的意愿和善意。
02
换个视角看待精神疾病,
你还会恐惧吗?
1.
精神疾病的发病因素中,遗传、基因等生理方面的原因占据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但在生理因素以外,养育环境、成长经历、创伤经验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这方面因素概括来说,就是一个人的成长背景:他是怎么样活下来的。
大部分严重精神疾病的患者都曾经历一些严重的创伤,比如:遗弃、虐待、严重忽视、性侵等。
他们可能长期生活在精神状态不佳,介于“有病”和精神病性人格之间的家属身边,承受着非常大的压力。
比如:有一个偏执型人格特征的父亲,经常一言不合就曲解事实,暴力制裁;或者有一个喜怒无常、歇斯底里,经常指责、抱怨、羞辱他人的母亲。
表面上,创伤往往和事件绑定在一起,有一个特定的剧情:谁伤害了谁,谁又被伤害了。这里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视角,因此每个人也有一个自己的剧本。所以,在剧情中拉扯,永远没完没了。
实际上,“创伤”的关键在感受上。感受中混杂着情绪,情绪出现之前是很多未被觉察的起心动念。
创伤就是指这些没被看到的、没被承认和接纳的,或是被刻意压抑的情绪能量和根植身体的身心反映。

创伤是普遍的,不一定都会引发严重的精神疾患,每个人都曾经历很多创伤。对大部分人而言,创伤引发的只是神经症水平的不健康,还算不上精神疾病。
然而,在神经症和精神疾病之间,并没有一道戛然而止的红线,有的只是在症状程度上和器质(指精神疾病在大脑、神经等人体内环境造成的改变)方面的差异。
注:神经症性障碍(neurotic disorders)或称为神经症,最初指相对较为普通的心理问题,个体没有脑异常的迹象,没有表现出广泛的非理性思维,没有违反基本的规范,但体验到主观的痛苦或自我挫败的模式或不适当的应对策略。精神症性障碍(psychotic disorders)或精神症,被认为在性质和严重程度上有别于神经性障碍。神经症患者的行为非常显着地偏移了社会规范,还伴有深度的理性思维和一般情感过程的混乱。1980年版出版DSM-III后,传统的对于神经症和精神症的划分就被取消了。
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用“谱系”来描述和界定精神疾病,将人类行为置于一整个光谱之上,从正常到非正常之间没有一个绝对的划分标准。精神疾病越严重,就越损害人的机体功能和社会功能。
所以,就我们每个人而言,在“有病”和“有精神疾病”之间,也没有一条绝缘线。
人们对神经症水平的“有病”习以为常,在争吵中可能会脱口而出:“这人有病吧!” 但却对精神疾病,尤其是严重的精神疾病充满恐惧,避之不及。假如自己患病了,也会有 “病耻感”。
这种恐惧和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受到对其了解程度的影响。比如抑郁症,从DSM手册上的诊断来说,两个诊断标准——抑郁发作和持续性抑郁症(PDD)都属于精神疾病。在十年前,假如一个人抑郁了,他可能就会被当做一个“精神病人”来对待。但在“996”“内卷”“躺平”等词语流行的当代,抑郁已经不是什么可耻的事了。
人们害怕那些行为明显易于常人的少数人,也害怕成为“少数人”。假如少数人后面还有极少数人,那最可憎最可怖最可妒的也往往是那极少数人。
人们也害怕不可控的事物。而精神疾病患者,比如精神分裂症患者混乱的行为中就代表着一种不可控的未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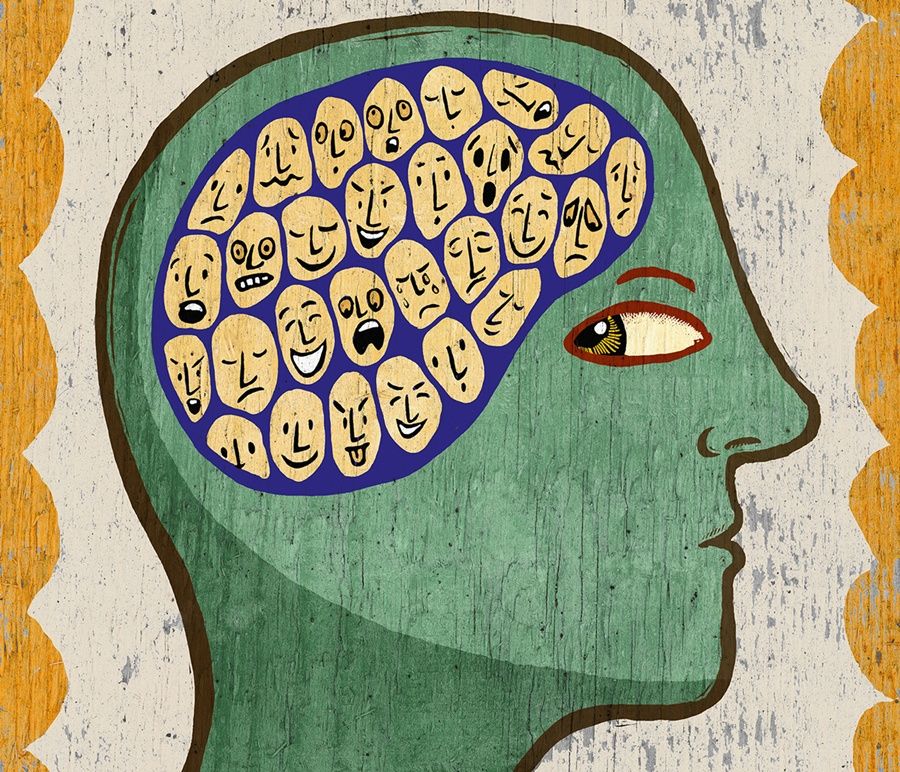
2.
我们想一想,一个粉嫩温香的小婴儿成长到一个罹患精神疾病的成年人,这期间发生了什么?在生理因素之外,是什么促成了这种结果?
压力和冲突日复一日地重复,假如情况很糟,超过了承受能力,一个困在这里的人需要做出怎样的“反应”才能让自己活下去?
他可能让自己成为了一个暴君,以暴制暴;他可能承受不住,直接杀了自己;他也许可以通过求助,或靠自己逃开了这个环境……假如这些路都行不通呢?一个人如何在压力长期超出承受能力的环境中生存?
疾病,或者精神疾病,可能成为一个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我们的身体远比我们所想的更智慧、更忠于自己。比如,抑郁就是最常见的一个“选择”,还有厌食症、强迫症、惊恐发作等等。
就像深海中的潜水员身负重压必须要有专业的设备才能存活,一个溺水挣扎的人也必须要有一根“救命稻草”才能继续挣扎下去。疾病形成了一种“平衡”,虽然看起来不可思议,但是事实就是如此。
所以,我们不仅要关注疾病所表达的,也要尝试去理解疾病所“承担”的。在某种程度上,疾病就是人应对环境的一种“创造”。
很多孩子出现心理问题的家庭都是这种情况。比如,父母情感失衡,面临离婚,或者一方有出轨情况。孩子如果承接到这部分的能量,他可能抑郁,严重点可能双相,或者他厌学,拒绝去学校上学。
所有这些都是无意识的选择,我们没有一个科学可验证的实验来“检测”这个动力,但这个动力是真实的,就在那里,等着被看见。我把这解读为生命自发做出的选择——为了和解,出于爱。

于家族而言,也有代际相传的“家族遗传病”,比如连续几代都有早夭事件发生,连续几代都有人死于某种疾病,也有隔代出现的精神疾病患者。
从一个家族能量的视角来看待这样的情况,家庭中“病” (这里主要指精神疾病)得最重的那一位,往往也是承受最多的那位,最有爱的那位。
承受什么?承受这个家庭/家族未被疗愈的代际创伤——那些冲突的、有张力的、未遂的情绪能量。它们可能是这一代的,可能是上一代的,也可能是往世的。
最终,精神疾病这个结果也许是不幸的,但它不恐怖,也不可憎。假如能够换个视角来看待它,看到它所承担的、它想要解决的,那么它可能就会转变成疗愈的巨大突破口。
(未完待续)

